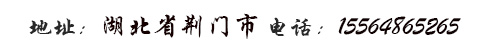陈徽隐逸传统和道家思想
|
补骨脂针剂 http://baidianfeng.39.net/a_wh/140111/4325346.html隐逸传统和道家思想 摘自《中国古典建筑思想四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第三章 陈徽(同济人文学院教授,古典书院教师)几千年以来,有两个传统始终和士人的生命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常使他们感到犹疑或彷徨,难以释然。此即隐逸与出仕,或曰“处”与“出”,两种传统展现了不同的生存情趣和处世态度。如何消弭生命中的这一分裂或对峙,也成为传统士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努力方向。仕的本义为做官,官有治众之义。出仕为官是为了协君理众,以达世治,故出仕与否当是社会分化特别是等级制出现后方有之事。世若得治,物阜民丰,教化流行,生生不已。对于士人(《说文》:“士,事也。”士谓善于做事者,亦即有才者)来说,出仕既是其人生职责之所在,亦是其生存价值之所依。据《尚书》可观:唐虞之世,帝者(尧、舜)致其身,尽心于治;臣者(如四岳、禹、弃、契、皋陶、夔等二十二人)竭其才,勤勉于事。君臣合心,以成至治(参见《尧典》、《舜典》),《皋陶谟》颂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唐虞之治对于后世影响甚深,士人论及,多有欣慕。晚周之际,面对乱世之状,诸子各开药方,孜孜进之,以尽其责。其间,固然在治道上存有差别,但诸子的救世之心则同。诸家中,秉持出仕精神且对后人影响最大者当为儒家。儒家认为,唐虞之世乃大道流行之治,故天下大同,万物生生(参见《礼记·礼运》所论)。然道非虚行,必依于其人。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又云:“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子夏亦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弘道是儒家自觉担负的存在使命。弘道体现在尽心于生生之事,“裁成辅相”(《易传·泰·象传》)、赞天化育(《中庸》),而尤以政事为要。顺此思路,子夏倡导“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实为自然。汉代以后,儒学独尊,百家之言多有衰蔽。在此情境下,出仕致用便成为大多数士人基本的生命态度。 石涛《悠然见南山》 隐逸与出仕相对,其之所以能成为传统,亦是渊源甚深。然与出仕不同,隐逸最初可能产生于衰乱之世,且表现为能仕或当仕而不仕,弃世而不顾。周以前,官皆世职,代代相袭。古代官职制度的这一特点,使得世职之士一般不会弃其职守,隐居不仕。而对于向来无世职可守的平民来说,其既无出仕之望,也就无隐逸之说。衰乱之世则不然:此时,礼崩乐坏,政治失序,官失其守,士丧其职。就此而言,早期的隐逸多有其不得已之处:隐逸者本来是想成就一番功业的,未尝有隐逸之志,然面对或凶险的处境、或难撼的势运、或因他事所迫,最后不得不归隐。比如殷末的微子之隐,即是因绝望、远祸所致。又如伯夷、叔齐之隐,他们本为避纣之暴而归服于文王,谁知后来武王翦商,代殷而立。尽管天下更太平了,但二人却无法接受武王的“臣弑君”之举,遂坚拒其召,不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直至饿死。还有如泰伯、仲雍之隐,亦属于不得已。他们本为古公亶父(周太王)的长子和次子,为成就太王立弟弟季历为后之志,遂避居于吴、越之地,以尽其孝。又如周衰,鲁国的乐官尝离散于四方,《论语》记云:“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微子》)这种离散极有可能属于归隐。特别是居于河(黄河、汉水)滨或海滨的鼓方叔、播鼗武、少师阳、击磬襄等人,应当即为隐居:早期的隐者往往择居于山水之旁,一为人迹罕至,一为风景绝佳[1]。又如虞仲、夷逸之隐,孔子评其行曰:“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论语·微子》)邢昺释云:“(二者)隐遁退居,放置言语,不复言其世务,其身不仕浊世,应于纯洁;遭世乱,自废弃以免患,应于权也。”[2]故虞仲、夷逸之隐也有被迫之意:生逢乱世,是同流合污还是自洁其身,二者必须作出抉择。选择隐逸,就是选择不与世俗合作,以高洁其行。较之于前四种,这种隐逸在晚周之际颇为流行。《论语》所记的隐者多属此类,如“石门之晨者”、“荷蓧丈人”、“长沮”与“桀溺”等。如果老子就是那个周太史儋的话,那么其隐遁当也有几分此意。 石涛《带月荷锄归》 还有一种自觉自愿之隐,或曰为隐逸而隐逸。此隐既非出于远害避祸,亦非坚执某种操守,而是完全为了追求乐道闲居之趣。如《庄子》以“颜回不仕”之例喻云: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让王》)在《让王》看来,道足以使人自乐,且此乐非出仕所能致。如果说此段文字尚显平和,以下文字已嫌乖张: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捲捲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让王》)《让王》此论已超出一般的出仕与否的界限:天下尚且不受,何况乎出仕!然其偏执之心亦因是而昭:既然唯有隐逸方能逍遥,则“处”与“出”便是绝对对立的。顺此思路,也就有了如下的极端之说,曰: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泠之渊。(《让王》)“北人无择”仅仅因为舜之让己以天下就“自投清泠之渊”,偏执之甚也!《让王》的这种坚执不通与庄子的灵动飘逸相隔玄远,故其所谓“逍遥”绝非是真正的逍遥。前文已云:逍遥并非意味着弃事绝物、隐遁弃世。同样,弃世不出也并非是通达逍遥的必要前提。若曰迫于某种时空情境,庄子可能会选择隐逸不出,然不可因此而谓隐逸便是庄子的基本立场。在论老、庄思想之同异时,钟泰指出:老子、庄子其学皆出于《易》,而《易》兼不易、变易二义。……老唯主不易,故静,静故“以物为粗”。庄唯主变易,故动,动故“不敖倪于万物”。“敖倪”犹傲睨,谓轻视之也。以“不敖倪于万物”,故“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故老子卒于隐去,而庄子则消摇人间,不屑为避世之士。[3]此说很是公允。而且,庄子尚有“明王之治”之论,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应帝王》)“明王之治”可谓是“逍遥之治”:在此治中,王者虽“功盖天下”、“化贷万物”,却又“立乎不测(言其化之神)”、“游于无有者”;生民虽性命各正,却又无所恃(“民弗恃”、“有莫举名”),若己自为(“物自喜”)。世之治若至于此,王与生民实皆入于逍遥之域。然而,《让王》的善卷之“入于山”、石户之农之“入于海”之说又表明:优游逍遥的人生境界似乎离不开与山水草木、鸟兽虫鱼的“亲密接触”。《庄子》云:“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秋水》)“儵鱼出游从容”,尚不可曰逍遥,此其本性使然,非为境界所现。所谓“鱼之乐”者,乃庄子所赋。而其之所以能赋于儵鱼以“乐”意,又在于其心感于儵鱼的“出游从容”之态,引发出优游无羁之怀。故逍遥之成深切于人与世界的生生之感,非谓枯坐孤寂之功。只有融入大化流行,体察物之天机自然,方可悟得逍遥之乐。 逍遥的生生之感性表明:无论意识到与否,人们的内心深处均怀有隐逸的冲动。在此冲动下,每个人似乎皆准备“遗落俗世”、“抽身而去”,在亲近自然中感受生命的自在。因为,“通天下一气耳”,人与万物本即是血脉一体、相互感发的:情因景而生,景因情而显,无论是“触景生情”还是“情景交融”,展现的都是情与景的互动互生。对于此“感应”,先民早就具有丰富而细腻的体会。《诗》中“比”、“兴”手法的普遍运用,即为其证。如《四牡》:“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翩翩者鵻,载飞载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将母!”鹁鸪(鵻)之飞翩翩自在,目睹此景,诗人却发出己身为王事所系而不得奉养父母之叹。又如《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倾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谓兮。”一位少女本来在收获成熟的梅子,随着梅子的纷纷落地,她却感物生情,叹息韶华易逝,遂有思春之意。或如《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以洋溢着晶莹露珠的蔓草与少女相配,不仅增益了后者的楚楚动人之美,且蔓草和露珠也散发出几分可怜可亲之意。《诗》中此例,不胜枚举。陶渊明有诗云“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之一),人是具有“亲近”自然的天性的。在此“亲近”中,人得以优游其心、涵逸其志,万物也皆富有情趣、天机无限。若无此“亲近”,人的生命意识与情感能力便不会得到真正的涵养和提升。 石涛《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亲近自然既为人之天性,则倡导积极出仕的儒家也不乏隐逸的冲动。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以水的流畅圆融和山的静穆浑厚分别喻示智者与仁者之德,显示了他对于以山水为代表的自然存在的深厚体悟。孔子欣慕那种“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式的优游之乐,深藏于其心的隐逸情结也不时萌动,随着在现实世界的屡屡失意,遂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如若为此,则夫子将与隐者何异?耐人寻味的是,江湖或湖海后来也成了隐逸的象征,成为中国文化中甚有意味的空间范畴。然孔子终究没有隐逸,大概是其使命意识过于强烈吧。对于那些因不得志而终不得不隐者,孔子也是充分理解的,尝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他很欣赏“处”、“出”自如的时贤蘧伯玉,赞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欲“处”而却“出”,展现了儒家在生存态度上的矛盾性:若“处”而不“出”,则与己之使命相悖;若“出”而不“处”,现实政治常却不尽如意,甚乃凶险。儒家的这种矛盾心态恰恰反映了其试图融“处”、“出”为一体的理想诉求:太平之治既表现为政治清明、庶民遂生、教化流行,亦表现为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彼此感发。在达此理想之前,则需孜孜以进。期间,固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尴尬或窘迫,然不可因此而懈怠。儒家既重“出”而甚于“处”,其于隐逸之心便多有抑制,以致世人常谓儒家是一味反对隐逸的。 在诸家中,真正将人性中的隐逸情怀充分激发出来的乃是道家。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展现了一个恬淡无为、虚静闲适的生存境界,其“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也颇具田园牧歌式的吸引力;庄子则以其浪漫的想象力为世人勾勒了一个无有羁束、优游天地的逍遥世界。如果说道家以前,士大夫选择归隐可能多少有些自发或被迫的意味,那么经过道家思想的“启蒙”,无论是被迫与否,隐逸之趣皆成为士大夫的自觉追求。魏晋之世,社会动荡,政治险恶。道家特别是老、庄思想深深地吸引了广大士人,催生了所谓的“魏晋风度”,隐逸之风遂益盛焉。 然浸淫于儒家思想既久,除了少数志气超绝者,慨然不复顾世而隐逸不出者,毕竟是少数。如何消弭“处”与“出”的对立,如何在出仕时也能体会隐逸之趣,便成为魏晋士人努力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思想领域,遂有“名教自然之辨”。此辨先是表现为“越名教而任自然”,最后归之以“名教即自然”。名教喻“出”,自然喻“处”。“名教即自然”乃谓“出”、“处”不二。“处”、“出”之间的分裂,终于在思想上得到了初步的消弭。 “处”与“出”的真正圆融是由宋明理学完成的。在理学家那里,无论是人伦日用,还是万物自然,无不体现天理流行。明道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4]人伦日用固需尽心,鸢飞鱼跃亦是体察天理的入手处。在《答横渠先生定性书》中,明道又曰: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应迹,一作物。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以反鑑而索照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如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诚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5]他还赋诗(《秋日偶成其二》)云: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6]可见,老、庄思想自然与自在的精神已被彻底地融入理学中了。只要心随道化,无私无智,“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便无物累之患、世羁之忧,随时彰显生命的优游自在。若心有偏执,即便是离群索居也未必能得逍遥之趣。实际上,宋儒也多精于此道,如明道观鸡雏可以体仁(按:明道常以生论仁)[7],而周濂溪不除窗前草、张横渠之观驴鸣,同样能悟得生生之理[8]。 在此之前,特别是魏晋时期,所谓“名教即自然”之说虽初步消弭了“处”、“出”之间的思想对立,现实中,归隐抑或出仕仍是士大夫的一个艰难抉择。既然作为儒者的使命感如此沉重,那么一种“权宜式的归隐”是否可能?循此思路,在种种努力下,遂引发了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向。 网师园 [1]如当初伯夷、太公避纣,便是选在海滨之处,《孟子》云:“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离娄上》)[2]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3]钟泰著:《庄子发微》,第页。 [4]程颢、程颐著:《二程集》,中华书局,年,第59页。 [5]程颢、程颐著:《二程集》,第-页。 [6]程颢、程颐著:《二程集》,第页。 [7]如明道云:“观鸡雏。此可观仁。”(程颢、程颐著:《二程集》,第59页) [8]明道尝记云:“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观驴鸣,亦谓如此。”(程颢、程颐著:《二程集》,第60页) 古典书院公益发展微店由学员自发组织,公开透明管理,义卖书院师生义捐物品,所得善款用于公益课程、会讲及非盈利性学术出版,谢谢支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angnaiqing.com/knxhy/5936.html
- 上一篇文章: 哪些花不能放在室内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