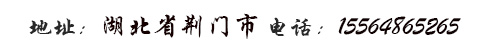美文不寐乃眠久
|
比起旁人,你才更像是我的一场冒险。 楔子 “听说这次上海那边的团队,总导演是耿京麒!” “耿京麒怎么啦?” “你不知道呀?他和咱们组鸥努好像关系不太一般……” 是听惯了的话,听得耳朵几乎生茧。 所以鸥努走进茶水间的时候,同事们纷纷噤声,她却兀自微笑着接了话:“他是我上学时的资助人。” 大大方方,堂堂正正。 如此,同事们没了八卦的心思,反倒像聊家常一般问起:“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她接水的手几不可见地一颤,摇了摇头,端着杯子往外走。那低声议论渐渐远了,直到只字片语亦听不到。 她走到廊中,四下皆静,而只有在这么静的时候,她才敢去想他。 想他和她之间的一切,究竟从哪里开始,一路行差踏错,以致走到了绝崖断壁,不得回头。 1那年,鸥努十五岁,居住在云南宁洱县。 偌大的村庄鲜有人来,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外务工,只留下老弱妇孺。村落与门户之间安静得让人生畏。她每日走两公里山路去学校念书,偶尔听到家中有电视机的同学黑子说,我们宁洱县上新闻了。 旁人好奇地问,因为什么? 黑子便抹着鼻涕笑嘻嘻地答,因为穷。 鸥努对“穷”这个字眼毫无概念,周围人的境况都大同小异,否则早就离开这里了。 就像隔壁的和英姐姐。 和英家一年前举家搬离了这个地方,临走前还送给她一个帆布书包,她一直背到现在。 “小鸥,你真该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和英说这话的时候,她正拿着帆布包,呆呆地红着眼眶不吭声。 和英姐姐生得很美,尤其是读了大学参加工作以后,再回来,已经完全和她记忆里那个有点脏兮兮的邻家姐姐不同了,那似乎是“外面”带给和英的改变。 可她自小长在普洱山侧,所见唯有泥土与树木、天空与飞鸟,从未奢望过离开。 后来,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几乎所有人都在议论。 “鸥努呀,有大城市里的人来了。”年迈的奶奶在灶前添火,偏头望着她。 于她而言,那就是和英姐姐说过的,外面的世界里的人。 她蹲在身侧帮忙扇风,闻言却只是咧着嘴笑,心里有说不出的好奇和兴奋:“他们来做什么呀?” “说是拍什么纪录片?他们说不定会到咱们家里来问,要是我不在,你可要好好招待人家。” 鸥努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奶奶,说了声“好”。 她等了两天,每天徘徊在门口那条土路上,直到天色暗了,才没精打采地回去,却整夜睁着眼睛,翻来覆去睡不着。 隔天上学时打瞌睡,额头撞在书桌上,黑子笑话她:“鸥努,磕头喽!” 她跟着呆呆地笑,也不恼。 再回家的时候,她走到家附近的土路上,很远便瞧见似乎是有明亮的灯光。那是她从没见过的,近乎刺眼的、惨白的光。高高的大灯照亮了不远处破败的景象,视线所及是一辆黑色的吉普车,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几个扛着机器、拿着本子的人站在周围,似乎在等什么。 鸥努咧开嘴,觉得很高兴——那些城市里的人终于来了。 她跑过去,衣着光鲜的男女便温柔地对她笑,将她围住,问她:“我们可不可以问你几个问题?” 她都不敢抬头仔细去看他们,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着点头,过了一会儿又摇摇头说:“等我一下,我要先打扫和喂猪。” 那些人很有耐心地跟着她,举着机器,记录下她所做的一切。她大概知道他们在拍自己,举手投足间多了几分不自在。 后来他们就开始问她问题。 “你的衣服为什么是破的呀?你挡着干吗?” 她拿手捂住了破烂的袖口,低着头不说话。 “你的妈妈呢?你的爸爸呢?你住在这里不害怕吗?这里这么荒?” 欧努垂睫愣了一下,咬住了唇。 “你天天都喂猪吗?不嫌臭?” 她终于扬起脸来看着对面的漂亮姐姐,眼神一片清明。对方被望得一愣,又接着问下去。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可怜呀?在这么不卫生的环境里生活……” 女孩干瘦的手指紧紧拧在一起,轮廓分明的小脸渐渐失去平和与微笑。她本能地感觉到了刺痛,却不知道是为什么。她觉得鼻头有些发酸,喉咙被一股不知名的热气哽住,连带着眼眶也开始发烫,发红。 她甚至不知道这就是对方想要的:她的痛苦,她的卑微,她的号啕大哭,甚至是不堪和丑态。 在听到对方追问“你多久洗一次澡”时,欧努终于如对方所愿地掉下眼泪,眼泪和面上的灰尘一起,化为最沉重和难言的卑怯。她被两三台摄像机死死地包围住,却已经不愿再抬头面对这些她原本好奇的一切。 没有好奇了。她想,我不会再好奇这些外面的人了。 然后她听到一个沉冷的声音说道:“够了苏奈,先不要问了。” “但是耿导……” “关机吧。” 她隔着泪花偏头望去,迷蒙的视线里,瘦削的青年正朝她走来,不顾地上的污垢,半跪在她面前,轻轻覆住她紧攥的拳头。 他仰面与她对视,眼神诚恳,他的掌心同她一点都不一样,柔软、细腻、温暖。 这是耿京麒第一次和她说话。 “抱歉,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哭吗?” 她在他的清俊气质前败下阵来,惶恐地挣脱开粗糙皲裂的手,随着动作,一滴眼泪砸在他白皙的手背上,灼得他心头一痛。 “因为你们……”她哽咽着,艰难地将话说完,“甚至都没有问一问我的名字。” 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面面相觑。 2“我叫鸥努。” 那是纪录片摄制组驻扎在村子里的第十天,耿京麒终于从闹别扭的女孩那里知道了她的名字。 那天她刚刚放学回来,在路口瞧见他,仍是一脸抗拒,甚至打算绕开他们回家。他只得拦在她面前,向她道歉:“对不起,是我们太心急了,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她站稳了脚,终于肯抬头看他。 耿京麒松了一口气,见她四下打量,又说道:“没有机器,这次就我一个人来了。” 他手里拎着一袋方便面,跟在她身侧,问道:“你喜不喜欢吃这个?我们也没带什么好吃的来,晚上给你煮这个好不好?” 最后当然是鸥努煮的面,他虽是二十出头的大人,却连烧火都做不好,更何况是用土灶大锅煮面。 耿京麒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这个还不到自己胸口的女孩熟练地烧柴,燃灶,起锅。熟悉的香味席卷而来,他忽地意识到,用土灶烧出来的饭菜的味道,大概和煤气是有些不同的。 似乎多了某种淳朴和迫切。 面盛在有了裂纹的陶碗里,再平凡不过的食物,此刻捧在掌心,却忽觉重得让他有些拿不稳。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女孩,看她在这破旧的屋舍里打点一切。原来,所有物件的摆放,都是她精心计算过的,连一帚一凳都盘桓再三。 她将瓷盆里的凉饭小心翼翼地端出来,问他:“耿先生,你要吗?” 那是生怕他拒绝的腔调,他忽地就心软了,点了点头:“我吃一点就好,你吃吧。” 女孩舀了一大勺饭,帮他泡在面汤里,喜滋滋地说:“我刚刚放调料的时候,就觉得就着饭一定很香,你试一试呀耿先生。” 那清澈的眼神,让他几乎忘记,几天前她还在他们的咄咄逼问下难堪地掉泪;几天前她还在难过,他们这样残忍而直接地窥视她的生活,却忘了问一声她的名字。 他几乎疑心她心里究竟有没有过“怨恨”“恼怒”这一类的情绪,此刻她坐在马扎上,捧着面碗大口大口地吃东西,偶然抬头看他一眼,就会露出笑容。那笑容像是一面镜子,将他打滚在软红十丈里,被迫染上的一身尘垢照得一清二楚。 他也因此不忍注目。 耿京麒有一瞬间哽住了呼吸,直到她问他:“耿先生,你怎么不吃呀?” 他才克制住胸口如压重石般的闷疼,勉强牵扯出嘴边一点弧度来,说道:“鸥努,你有什么愿望吗?” 只要他可以做到的。 女孩咽下一口食物,捧着碗呆呆地看了他一会儿,终于展颜。 “有。” “什么?” “跟我讲讲外面的生活吧。” 3纪录片摄制组的所有人都觉得,耿京麒在“和村民打好关系取得信任”这件事上,似乎有点过了头,并且还有点本末倒置。 这次摄制组驻扎到村子里,分了三个Team(团队),各有选定跟踪拍摄的主人公。耿京麒是总导演,他对责任编导苏奈说,他亲自来跟B组鸥努的采访。 可是几天过去了,耿京麒不但没说开机,和鸥努的聊天内容基本在讲上海的都市生活,甚至还给她看了不少相关视频。 苏奈和摄像大哥吐槽,本该是他们去问人家的生活,怎么到了鸥努这里就倒过来了? 不开机又从哪里来素材?可是一大一小在板凳上专心致志地聊着天,像是完全忘了还有拍摄任务。 鸥努觉得这几天的所见所闻恍然如梦。她在耿先生的手机里见识到了所有无法想象的事物:灯火璀璨的外滩夜景,旧事沉淀的石库门……动态的视频构建了她向往的一切,她陷入他在新年倒计时拍摄的焰火中,痴痴地问:“这是什么?” “跨年。” “以后我也有机会这样跨年吗?” 耿京麒沉默地凝视她良久,才说:“会的。” 那盘桓在心口中的一句话迟迟未能出口,他偏头望见在旁边百无聊赖等待的摄制组,终于还是呼出一口气来,接着问道:“鸥努,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 女孩想也没想就点了头,他反倒一怔。 “谢谢你,耿先生。”她分外诚挚地望进他的眼里去,有一抹光亮瞬间穿透了他浑浊的瞳仁,“你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接下来的跟踪拍摄无比顺利。那些难堪的问题,让她不安的日夜注视,渐渐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苏奈开始佩服起老大的先见之明,如果浪费几天时间能让以后的工作进行得事倍功半,那当然是明智之举。 可事情并没有一直顺利下去。当苏奈试图让鸥努表现出“呼喊”“痛哭”或是“独白”之类的特定情境里的情绪时,女孩却抿着唇拒绝了。 “我不会演戏。” “这不是演戏,鸥努。”苏奈尝试着去解释,“这是因为我们剪辑需要一些素材,不用你去假装,因为这也是真实的你不是吗?” 她被摄像师和苏奈围住,扬起头,视线从他们的面上扫过。 她知道他们渴望某些东西,他们希望她像个疯子一样大哭、大闹,跑在山路上悲泣命运的不公;他们希望她独自在深夜里做出瑟瑟发抖的模样,再念出他们写出的独白,如同一个演员——将她内心不肯展露的悲哀,以这样戏剧的方式,残忍地、血肉淋漓地表现给看客看。 她想,耿先生一定和他们不一样。他尊重她,没有将她当成异世界的怪物来观察她的一切,他只是用平等的、温和的视线注视她,告诉她她想知道的一切。 外面的世界里,只有耿先生是不同的。 她摇头,再摇头,最后红着眼眶推开这些咄咄相逼的人,跑出了房间。 “鸥努!你去哪里!” “天都黑了,鸥努!” 她跑得很快,脚上一双旧运动鞋已经破了几个洞,有寒冷的风灌进来。她穿一身缝补过多次的粉色夹克,仗着对地形的熟悉,拐了几个弯,将他们甩在身后。 风渐渐大了。深秋季节,山里总是湿气很重,仿佛穿透衣衫,浸入了发肤。 不知过了多久,她猜想他们或许已经走了,于是悄悄返回。崎岖的山路上留下她或深或浅的脚印,走了一会儿,有手电筒的光亮在远处闪烁,跟着传来人说话的声音。她站住脚,躲在了一间废弃的屋舍后头。 那是她刻在骨子里的,耿先生的声音。 “我花了那么大力气才和她混熟,让她配合一点,这才拍了几天,你们就又把人给惹毛了?我说过多少次,让你们慢慢来,别着急!” “耿导,我没着急!我也不知道是哪句话没说对,她就跑了!” “算了。”他的语声沉冷、寒凉,与从前同她对话时的温柔截然不同,像是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人。 她听到脚步声近了,他低声说道:“我会想办法让她做出效果来。” 鸥努躲在墙后,捂着口鼻,愣怔地将喉咙里的哽咽给吞了回去。在手电筒的光亮照进视线的前一秒,她跌跌撞撞跑出来,与他们狭路相逢。 “鸥努!你怎么在这里?” 女孩抬手遮住自己的眼睛,以免被那强光刺得掉下泪来。 “我刚刚才走到这里。”她低声又补了一句,“好巧啊。” 这么巧,她只是刚刚走过来,所以他说的话,她偏偏一个字都不曾听到。 4B组的跟踪摄制再次顺利进行下去。 苏奈无从得知,老大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才让鸥努终于松口同意做一些效果出来。可当她旁敲侧击问起时,耿京麒却沉默良久,摇了摇头:“我什么都没做。” 一伙人正收工吃饭,围坐在一处,听到耿京麒这句话,都略感震惊地抬头注视他。 耿京麒面上有不易察觉的自嘲。他停了一想,才接着说道:“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开口,她就去找苏奈说同意了。” 他说完这话,沉默地撂下碗筷,走了出去。 他驱车回到鸥努家附近,下了车,却迟迟没有过去。摄制组的居住环境并不好,但比起鸥努的家,却堪比豪华套房了。那间屋舍颇像戏文里唱的残垣断壁,他甚至害怕哪天下了雨,摇摇欲坠的屋顶会砸落下来。 而她就在这样的危房里住了十几年。 他拍这部片子的初衷,是想唤醒社会对山村里留守儿童的关怀,可渐渐地,那初衷变了,变成了填不满的欲壑——这是他入台第一个担当制片人和总导演的项目,所以他一定要做好,不然无以立足。 “唤醒”这两个字本身,最终没能赢过“名利”。 他站了太久,久到脚底有些发麻,指间一支烟烧尽了,烫到皮肤,他才猛地回过神来,听到有人在叫他。 “小伙子。”几步之外,白发奶奶穿一身哈尼族的衣服,用不甚标准的普通话唤他,“外面冷呢,你进来坐坐吗?” 他迎上对方毫无杂质的视线,不由自主地挪动了步子。 走进熟悉的屋内,设置在里面的几台机器还在运作,他循着职业本能用眼神确认了一下机位,才问道:“鸥努呢?” 奶奶指了一下里间,有微微的烛光透过来,摇曳着一道影子。 他走到门边,看到她正蹲在椅子边上写作业,早已写满了的草稿纸上是密密麻麻的演算公式。她分明知道他来了,却不吭声。他走近,站着看了一会儿,拿过她的笔,重写了一个算式。这次代入进去计算,终于算对了。 女孩咬着下唇盯了一会儿,才抬头看他。 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眼神也与半个月之前初见他时要变了许多。 “你需要我再发一次疯吗?”她咬着唇,却牵出一个笑来,“苏奈姐姐说,白天录的那个不太到位。” 他有一瞬间愣住了,等反应过来,她已经冲了出去,准确地找到机位,拉住奶奶开始号啕大哭。她的喊声是那样凄厉,嘴里叫着“奶奶你别走”“我一个人害怕”。如果不是他前一秒目睹了她的平静,他几乎要以为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可是不对,不应该,不能够。他有一瞬间蒙了,动作却先于理智,几步冲过去把她拽住。 “鸥努!别这样!鸥努!够了!我们不用再拍了!” 奶奶无措地站在一旁,流下两行浊泪。而她似乎是累了,终于在他的两臂之间渐渐平静下来。他俯身将她紧紧拥住,她的热泪便透过衣襟浸湿了胸口。 他被那温度烫得松开手来,与她对视。 昏暗的屋子里,有摄影机转动镜头的声响。他知道监视器那头必然有人在注视着这一切,注视着他是如何亲手逼她变成如今的模样。 她神色平和地流着泪说道:“耿先生,能帮你的,我也就帮到这里了。” 空气仿佛凝滞了。他知道监视器那头是怎样的骚乱,也知道苏奈此刻或许已经心急如焚,生怕B组的摄制会因此夭折。 然而此时此刻,他只是克制着表情,用异常冷静的口吻否认:“这句话不对,鸥努。” “我给你看了外面的世界,却没有讲外面的人。”他轻声说,“他们不习惯‘帮助’,习惯的是‘交换’。所以你要记得问,‘我帮了你,你能给我什么’。这样,以后你到了外面,才不会像今天这样伤心。” 鸥努看了他一会儿,终于缓缓张开双唇:“我帮了你,耿先生,你能给我什么?” 他此生罕有窘迫,那一天,那一夜,却因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小女孩说了一句成熟而凉薄的话,连隐忍亦不能,任凭赧然溢出容色。而她的灼灼目光,仿佛一把利刃,直直地戳进他胸口。 时至今日,还尚有余痛。 5耿京麒的纪录片甫一上线,就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讨论,而主人公之一鸥努,也成为热门人物。 各路媒体深入宁洱县的村落,只为了一篇鸥努的追踪报道。媒体称她为“掉落深山的仙女”“坠落凡间的天使”,因为她明亮而赤诚的眼神,照出了世间百态的丑恶,令人不堪自视。 渐渐地,有人通过相关机构申请资助鸥努。公益机构通过筛选,向鸥努推荐了一位出资人魏先生,还为他们牵线搭桥,约定见面。 这两年,鸥努因为总是受到媒体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angnaiqing.com/knxxx/62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