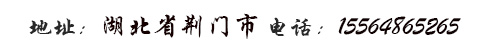雪虫日樱木紫乃短篇小说
|
香港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 http://m.39.net/pf/a_4618888.html 天空一片晴朗。今年最后一茬牧草已经收割完,村子里也变得冷清下来。十月,秋风掠过,给收割完牧草的十胜平原带来鲜艳的色彩。 牛棚二楼堆得满满的青贮饲料正在发酵,散发出一阵青草味儿。这牛棚顺着丘陵的倾斜地势而建,从正面看有二层楼,从背面看却是平房。二楼的门板被拆掉了,柔和的阳光能照进来,而且很通风。 达郎躺在一块铺席大小的空位上,仰望着堆得高高的打成块状的牧草。他身旁搁着红褐色的工作服。对面,是下半身裸露着的四季子。达郎心不在焉地看着她的腰。她背对着他,忙着清理完事后的现场。 缠绵过后,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青草和汗的混合气味。四季子感觉到达郎的目光,便回过头来。她的脸上没有化妆。 “怎么啦?” “没事。” 干农活不需要化妆。但她看起来依然妩媚,大概是因为达郎见过她精心打扮的样子。达郎和四季子都是在当地高中毕业后就离开了村子,去札幌 两人二十四岁的那年春天,四季子刚高中毕业的弟弟发生车祸,年纪轻轻就死了——深夜飙车时转弯不及,个人的全责事故。 “我要回乡下去了。” 在昏暗的床上,四季子背对着他说。 当时,整个社会都沉浸于一派繁荣景象之中。刚进房地产公司的达郎也不由自主地飘飘然起来。即便是相处多年的女人提出分手,他也随口就答应了。他心想:能取代四季子的人可多的是。 “没办法,谁让我是养女呢。” 关于四季子是养女这事,村里人都知道,虽然没人当面说。 四季子把纸巾揉成一团,塞进工作服的口袋里。她用手指弹了一下达郎的大腿。 “别老是露出那玩意儿,赶紧收起来吧。” “那玩意儿……还真是失礼了。” 离开札幌时的郁闷心情早已经消散了。达郎爬起身来,一边小声嘀咕着,一边开始整理衣服。四季子看了看太阳的方位,说:“我得回牛棚去了。”农村里用不着手表,根据季节和太阳的倾斜度就能安排农活。 四季子回村刚过两年,达郎也回到了乡下。由于泡沫经济崩溃,他的公司才成立一年就亏得一名不文。好在他没用父亲伸二的名义为公司担保,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看到生病住院的达郎,父亲说道: “算啦,别干了。” 经营状况好的时候,达郎觉得村里的一切都可以抛弃,甚至包括父母。而他回村里后,却要依靠父母养活。一晃十年过去,达郎已经三十六岁了。 受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疯牛病的影响,养牛农户们的经营状况越来越窘迫。不过,只要达郎和父母一家三口不大手大脚,勉强糊口还是可以的。在这个多达三分之一农户弃农离村的时代,这已经算相当幸运的了。达郎申请自愿破产后的一段时期,曾经屡次遭受债权人骚扰并为此大伤脑筋。而最近几年,他们也没有再来找麻烦了。 达郎回村的两年前,四季子生下了一个男孩。听说,她丈夫比她大两岁,从京都来村里农业实习时被招为了上门女婿。 “四季子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了哟!” 达郎刚回村里,母亲就有意无意地提醒他。达郎和四季子的关系,从高中起就是村里茶余饭后的话题之一——乡下人唯一的娱乐,就是议论别人的八卦是非。他俩正因为厌恶这一点,所以当初才逃离此地。达郎破产后回乡时,心中无比凄惶。而现在借着和已嫁为人妇的四季子的相互温存,他渐渐平复了下来。 “幸亏生的是男孩。” 四季子对达郎说道。这样,只生一个就完事了。生个男孩接替已死的弟弟,以此报答养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自己被赋予的唯一任务。当初听到四季子的这番话时,达郎只是付之一笑。然而,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今他再也无法一笑了之。像他这样一直不娶媳妇的话,牧场早晚要落入别人手中。对于年迈的父母来说,继承人问题是个无论白天黑夜都时刻惦记着的心结。 久违的四季子的身体越发成熟了。达郎看着她那坦荡的表情,心中不由感到踏实,但同时又为她的淡漠而有些害怕。对她来说,按父母的安排结婚,并如父母所愿地生下男孩,似乎就只像换个工作一样轻松。 “没办法,谁让我是养女呢。” 四季子若无其事地从后门出去了。她从衣袋里取出袖套戴上,穿过两块防风林,走回家去。开车的话不用一分钟就到了,走路大概需要七八分钟。达郎也沿着细长的梯子爬下牛棚一楼。趁着父母午休而跑出来幽会的短暂时间就这样结束了。 达郎家距离牛棚五十米远。他回到家时,看见门口停着一辆白色轿车。这车看起来有点儿陌生。他走上前,向车内窥视——后排座位上乱扔着地图和信封。好像不是兽医的车。 他脱掉沾满干草的长靴,走进厅里。里面来了客人。客人坐在父亲伸二对面,大概五十岁左右,浅黑色的脸上戴着一副蓝色墨镜。达郎立刻感觉到:自己以前炒房时,就曾经见过这种人。 客人轻轻地点头行礼,然后转向伸二,恭恭敬敬地问道: “这位是您儿子吗?” 伸二背对着达郎,点了点头。厨房里,母亲和子背对着客人,手上不知在忙着什么。她似乎不太欢迎这位客人。 伸二从矮饭桌下取出一个褐色信封,递给那人。那人接过后,打开信封确认了一下。从他的动作不难看出来,信封里装的是钱。从厚度来看,有一百万日元。泡沫经济时期另当别论,但如今,农家养牛是绝对卖不出这么高价钱的。那人默默地微笑着,看了达郎一眼。 “那我就告辞了。”他站起身来,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经过达郎面前时,他那锐利的目光透过墨镜扫视过来。达郎根本就没想跟他打招呼。 送走客人后,伸二回到厅里。在厨房里的和子也转过身来,似乎有话想说。达郎忘记了体内残留的疲惫,来回打量着父母。 “我不赞成这么做。” 和子先开口了。伸二别过脸去,回了一句: “那也没办法呀。” “应该跟我和达郎好好商量一下嘛。” 和子的声音像金属一般具有穿透力。达郎突然听到自己名字,不由感到几分惊慌。 “跟我有关系?” “你爸说要给你买个媳妇回来。刚才那个人就是拐卖女人的人贩子,卑鄙无耻得很。” “怎么没人跟我提过这事?” “不就是在农协定期体检时查出两三颗息肉嘛,就这么紧张。反正,什么鬼媳妇,我是绝对不认的!” 和子激动不已地嚷着。这些情况,达郎全都是头一次听说。 “闭嘴!” 伸二低声怒吼道。 其他事情也就算罢了,但现在是给自己找媳妇,所以达郎也不能再装聋作哑了。他从没想过他们会瞒着自己偷偷办这事。 “爸,虽然我没资格说三道四的,但至少你也得先跟我说明一下呀。” “再过一阵子,咱家媳妇就要上门来了。我一抱上孙子,就可以退休了。” “是我的媳妇?” “当然。” “为什么决定得这么仓促呢?” “如果我不在的话,光靠你娘儿俩能看住这些牛和地?抱上孙子,我死也就瞑目了。” “你说什么?那钱是定金吗?到底要花多少钱?”达郎怒吼道。 “这你别管。”伸二不肯回答。 这时,和子从旁插嘴道: “说是要三百万日元呢。” “三百万日元,买哪里的女人?” “说是菲律宾的。” 就这么呆站下去,显然也只能是在原地兜圈子而已。谁都不肯让步。简直让人晕头转向。对于达郎来说,最吃惊的并不是他们瞒着自己找媳妇,而是父亲竟然如此担心健康问题。这么着急要找儿媳妇、抱孙子,大概是因为年纪关系吧——父母都已经六十五岁了,这几年来头发也白了一半。 定金已经付了。事到如今,就算推掉这事,钱也拿不回来了。在令人压抑的沉默中,达郎感到无地自容。自己曾经离开这片土地,然后在走投无路时被父亲带回家来。面对渐渐老去的父母,他说不出“别指望我啦”这样的话。现在每天都在村里悠闲地混日子,然而终有一天,自己也会变老的。 即便如此,达郎还是觉得不可思议——看准农家娶媳妇难而做这样的营生,他原来一直以为这种事情只存在于电视和电影里头,想不到竟然存在于现实中。他回想起刚才那个人的锐利眼光。看来,只要肯给钱的话,娶媳妇、抱孙子什么的,全都不在话下。 照这样下去,无论再等多少年,也不会有哪个古怪的女人愿意嫁到家里来。达郎每天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混日子,对生活逆来顺受。愿意嫁给他的女人,要不就是看错人,要不就是看破红尘了。而且,父亲一旦发现他和四季子又黏在一起的话,肯定会越发感到不安吧。 “我无所谓,哪里的女人都行。给你们生个孙子就是了。” 达郎心想:答应就答应呗,反正每天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话说出口了,心情也就平静下来。当然,他说出这句话,并不是出于孝心,而是一种顺水推舟似的狡猾。 和子放声大哭起来。 太阳渐渐西沉,照在走向牛棚的达郎的后背上。以前要挤牛奶的时候还挺费力气的,不过现在改为专门养牛之后,工作变得轻松了很多。父亲养的十胜牛也曾在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既然过上了安稳日子,自然也就想给儿子娶媳妇、抱孙子——父母的想法无可厚非。 看见母亲哭泣、父亲沉默时,达郎却觉得这些似乎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忽然,他想起了四季子——当她面临着要和周围人给她安排的男人结婚生子的命运时,也是这样逆来顺受的吗? 想不到两人的境遇如此相似…… 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像蚂蚁一样过着卑微琐屑的生活。日子久了,连心情都会被大自然逐渐压垮的。就和那收割下来的牧草一样——发酵,增加养分,最终变成堆肥。身心一起腐烂,化为土壤。那样也不错。对于达郎来说,活着已经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从申请破产免责那天就已经失去自己的意志了。 风变冷了,吹得人皮肤干燥。四季子双手趴在堆得高高的青贮饲料上,达郎在她后面。当他让四季子配合自己一些的时候,四季子显得很不耐烦。和年纪相仿的女人相比,四季子要高出半个头,所以她经常穿男装工作服来掩盖修长的腿。达郎一直觉得,让四季子摆出这种姿势是最舒服的。 达郎的动作慢了下来。四季子一边喘气,一边说道: “喂,你打算要养那个菲律宾女孩儿了吧?” “跟‘养’有点区别吧。” “那是要跟她结婚?” “嗯,是这么说的。” 一想到四季子可能会吃醋,达郎不由感到大腿根部一阵酥痒…… 汗水很快变冷,干掉了。随着天气渐冷,也不能每次都这样裸露着下半身来感受季节变化了。四季子背部起伏着,收拢了双腿。 “天气慢慢变冷了啊。下次改在车上吧。” “没有下次了。” 四季子一边穿上内裤,一边断然说道。 听到这句意外的话时,达郎有些不知所措。 “‘没有下次’是什么意思?” “我不会再来这里了。” “不就是花钱买了个女人嘛,这也不能怪我呀。” “你别自作多情。不是这个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达郎还从来没有想过要分手。他原以为,无论过多久,他和四季子之间的关系都永远不会结束,两人会以相同的速度发酵、腐烂、化为泥土…… 四季子停顿了一下,瞪了达郎一眼,说道: “那女孩被卖到国外来,连话都不会讲哟。如果你不保护她的话,还有谁能帮助她呢?” “这是两码事呀。” “没法当作两码事。” “我还是我,什么都没变呀。我会处理好各种关系,不会冷落了你的。” ——当初,在四季子要离开札幌回村里时,如果自己对她说了这句话,不知道两个人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想到这儿,达郎很快就打住了。 “达郎,我和那个女孩都不是牲口。” 说完,四季子向门外走去。达郎连忙抓住她的手。四季子猛地回过头来。两人互相对视着。 “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呀。” 四季子说道。达郎以为她哭了,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四季子笑了。 每次她像念咒语似的说出那句“没办法,谁让我是养女呢”时,脸上就挂着这样的无奈的微笑。牛棚里只剩下达郎孤零零的一个人。他踉跄着坐在一块滚到旁边的四方形青贮饲料上。 一星期过去了。就在达郎接连三次预感到“今天就会上门”而落空时,他又看见那辆白色轿车停在了家门口。 从牛棚窗口向外望去,一片泛黄的景色——说明冬天已经临近。眼下这季节,应该很快就能看见雪虫 轿车里走出两个身影——一个是上次见过的那个人,另一个则瘦小得多。逆光看不太清楚,大概就是那个女人吧。伸二从屋里走出来,连连点头。那男人推着那瘦小的身影往前走。 今天,达郎喂牛特别认真,而且也比平时喂了更长时间。他不想让别人以为自己那么着急回家去。其实,在为即将到来的拖累感到焦躁不安的同时,达郎也有那么一点点的欣喜。他期待着也许时间能够改变一些东西。各种情感互相交织、纠结在一起,在他心里渐渐积聚起来。 达郎回到家门口,拍掉工作服上的灰尘。这时,那个男人从客厅走出来,说道: “辛苦啦。每天都这么忙啊。” 他的语气并不恭敬,似乎隐含着“又不是你出的钱”的意思。达郎并没有搭理他。当那男人穿上皱巴巴的皮鞋时,他的夹克衫内袋露出了一个和上次一样的褐色信封。——应该是一手交余款,一手交人吧。伸二要送他出去,他一手拦住,然后慌里慌张地上了车。达郎看着车在尘土飞扬中远去,方才走进客厅里去。 那个瘦小的少女站在窗户前,乌黑茂密的头发在脑后扎在一起。跟想象中的截然不同——皮肤比想象中的更白。她把细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达郎。达郎心想,跟自己在札幌见过的那些菲律宾妓女大不一样。她这副模样,说是日本的初中生也不会有人怀疑吧。 秋天快过去了,而她还穿着廉价的短袖T恤和露出膝盖的牛仔裤。少女无聊地呆站着,达郎看着她那瘦小的身体,不禁感到失望。在达郎看来,她并没有一个成熟女人的体态。她用求助的眼光看着达郎,脆生生地说道: “你,好。我,是,玛丽。” 声调偏得离谱。见达郎没有反应,她又从头说了一遍。达郎想说点儿什么,但却说不出话来。伸二和和子也呆呆地站在原地。达郎看了看母亲——她是因为听到“抱孙子”才勉强答应下这事的——此时,她整个人都无精打采,脸上的皱纹也变得更深了。已经准备好迎接媳妇的全家人都大失所望。 “说是才十八岁。” 伸二的手里攥着一本护照。达郎脑里浮现出那个男人的狡黠的笑容。事到如今,也只能把这少女留下了。达郎想说:“这还不如找个马贩子呢。”但还是咽了回去,改口说道: “早知如此,一开始就买个孙子回来多省事呀。” 和子默默地走进厨房。她向来如此。每次碰上不顺心的事、令人恼火的事,她就一定会走进厨房里,然后背对着这边,把所有烦心事都冲进下水道。这是她在这片犹如牢笼般的土地上保护自己的方法之一。 伸二坐在那张几十年都没变换过位置的黑皮沙发上。沙发有几处弹簧露了出来,变得凹凸不平。但从来没有人指出来,也没有人提议要买张新沙发。伸二一脸茫然地看着那本护照。达郎看见了父亲手上出现的老人斑。玛丽觉察出大家的失望之情,便殷勤地向他们逐个点头鞠躬,说道: “请,多,关,照。” 她对着达郎鞠了两次躬。 没过两天,大家就发现:原来玛丽只会用日语说几句问候语,而达郎说的话,她几乎一句也听不懂。达郎想吩咐她做点儿什么,比如让她打扫一下牛棚,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于是,她就越发焦急,越发卖力,想得到别人的一句半句赞扬。结果,连等吃饲料的牛都被弄得紧张兮兮的。而达郎嘛,嘴里蹦出一个个初中学过的英语单词,但还是跟对方沟通不了,于是也变得焦躁起来。 如果她懂一点儿日语,懂得讨人欢喜,再懂得唱唱歌跳跳舞,那么她的命运也许会不一样吧。如果她再风骚一点儿,说不定还能自己挣钱,大摇大摆地回国去。白皮肤和细长眼睛虽然是日本人喜欢的类型,但在这里,却无助于她自食其力。 玛丽从上门那天起就住进达郎的房间里。达郎仍然像以前一样,睡在从高中时期使用至今的单人床上。玛丽则在床下空位处铺了张褥子。达郎只觉得麻烦,却感觉不到欲望的蠢动。 即便如此,玛丽还是整天都寸步不离地跟着达郎,一起乘坐拖拉机,一起去牛棚。达郎心想“反正沟通不了”,于是也就放弃了,整整一星期都几乎没对她说过话。玛丽感觉到被忽略了,就默默地走到牛棚角落,或是待在圈养牛犊子的栅栏里,等待达郎的心情好起来。 不经意间,达郎忽然看见玛丽正学着他平时的做法给小牛犊喂牛奶。看见这温馨的画面,达郎渐渐平静下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此刻的心情。“哎,真麻烦。”这么一想,他连忙移开了视线。 四季子会不会冷不防地跑来这里呢?达郎心里仍然抱有这样的期待。只要看见玛丽,她就会明白的。一想到不能再和四季子见面,达郎就更加热切地怀念起她那温暖、润泽的身体。 “我和那个女孩都不是牲口……” 达郎耳边不断回响着这句话。想到四季子,他不由对这瘦小的菲律宾女孩子充满了厌恶。 忙完牛棚里的农活、回家吃晚饭,总是要到八点左右。当晚也一样。盘子里盛着满满的干烧菜和油炸食物。大家都厌倦地拨动着筷子,只有玛丽吃得很起劲。自从她来了之后,吃饭时间就变得更安静了,每个人都默默地吃着。玛丽也学着达郎的动作,笨拙地用筷子夹菜送进嘴里。她越是表现得快活,饭桌上的气氛就越是凝重。伸二和和子一直低着头,只是偶尔偷偷地看一眼那两人。 电视屏幕里正漠然地播报着新闻。这时,门外传来停车声。接着,门打开了——是四季子。 “不好意思,打搅了。” 四季子打了声招呼。和子放下筷子,看了一眼达郎,然后一边答应着,一边慢腾腾地站起身来。伸二仍然顾自吃饭。 “我妈让我把这个送过来。” “哎哟,谢谢啦。已经到这季节啦。每年一收到这什锦酱菜,天就变冷啦。” 每到这个时节,村里的女人们都会互相交换自家拿手的腌咸菜。这是当地长期延续下来的习惯。收割完后,女人们就要为过冬做准备了。 “我家的腌咸萝卜,还要再压一压才能拿出来。寒冬前我会让达郎送过去的。你跟你妈先说一下吧。” 两人的对话似乎有些生分。忽然,和子提高了嗓门: “噢,你还没见过呢吧。稍等一下。” 和子把玛丽叫到门口。达郎知道母亲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冷淡,便停下了筷子。玛丽一溜烟似的走到门口。达郎也站起身,跟上前去。 “这位是我家媳妇玛丽。你们年轻人的事,我啥都不懂。四季子,你可要多教教她哟。” “我,是,玛丽。请,多,关,照。” 她点头鞠躬时,扎在后面的头发甩了起来,从达郎的胳膊上拂过。 “不客气,请多关照。” 四季子若无其事地微笑着。达郎见状,一股难以名状的怒气油然而生。母亲的言行也同样让他感到恼火。 村子里,女人们之间的互相来往就像这样延续至今。只要生在这片土地上,无论今天、明天,甚至子孙后代也会互相联结在一起。达郎不由回想起来,自己当初正因为难以忍受这种人情纠葛,所以才决定逃离村子、前往札幌的。 他朝身穿长袖运动外套和牛仔裤的四季子瞪了一眼。四季子向玛丽轻轻地挥了挥手。 “再见啦。阿姨,有空就来我家坐坐呀。我妈也挺想你的。” 和子连说了好几遍谢谢。达郎心里忽然产生了想一脚踹在母亲背上的冲动。他还想责问四季子:难道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达郎取下挂在门口横梁钉子上的摇粒绒羽绒外套,对四季子说道: “你顺便载我去一下镇上吧。” “可以呀。不过,你怎么不自己开车去呢?” “我喝了点儿酒。” 达郎穿上运动鞋。平时,只喝这么一小瓶啤酒的话,那根本就不叫喝酒。但现在达郎想不出别的借口来。 “达郎!” 伸二在客厅里怒吼道。达郎没空搭理他,现在眼睛里只有四季子。和子也想叫住他。达郎用力拉上了大门。 呼出的白气仿佛被星空吸走了。明天可能会打霜。到十公里外的镇上,只需要开十分钟。迎面开来一辆打着远光灯的车,四季子怒气冲冲地直闪车灯。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还想问你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 “后来你怎么没再去牛棚了?” “我不是说过了嘛。你还要让我再说多少遍呀?喂,要送你到哪儿?快说!” “别岔开话题。” “谁岔开话题了。我只是来送个咸菜,哪有这么多时间带你兜风。别老是只顾自己。” “你为什么要到我家里来?” “你是责怪我不该来送咸菜?” “你可以趁明天我不在的时候再送来呀。” “你想说什么呢?” “你是想来见我的吧?” “又来了。你能不能别再自作多情了?” 车来到通往镇上的十字路口。 “向左拐。” “向右拐才是去镇上哟。” “你别管,向左拐就行。” 四季子不太情愿地改变了路线。公路右边闪过一家超市、一家便利店、点心铺、杂货店……这些商店基本上都可以满足生活所需了。但达郎想要的东西,这里却买不到。车离镇上越来越远,驶入一条和农用小路交叉的昏暗的路,然后停了下来。车灯照亮了路边,干枯的杂草正柔弱地随风轻摆。 “到底要送你到哪里?” “去情人旅馆。” 街上只有一家情人旅馆。两人还在读高中的时候,一户弃农经商的人家就开始经营这旅馆了。当时,周围的人都用很难听的话咒骂他们。然而,二十年过去,这家旅馆仍然还在营业,可见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别开玩笑了。你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吗?” “那你明白我吗?” “我没法明白。” 沉默片刻之后,达郎声音嘶哑地对四季子说道: “不明白就算了。带我去情人旅馆吧,拜托了。” 于是,四季子又亮起车灯,踩下油门。 情人旅馆果然如想象中的一样破旧,似乎已经多年没有重新装修过了。即便如此,总共六间房当中,有四间都有人用着。两人进了一间日式房间。整间房都潮乎乎的,墙壁散发出洗涤剂、香烟和汗水的气味。 四季子并没有掩饰马虎草率的态度。她甩开达郎的胳膊,自己脱掉了长袖运动外套、牛仔裤和内裤,全都扔在床边,然后扑通一声仰面躺到床上。乳房无力地垂向两边。达郎也脱下衣服,扔在满是烟头烧焦痕迹的榻榻米上。然后,他用双手按着四季子的肩头,俯视着她的脸。四季子也仰头直视着他。 “喂,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不知道。” 达郎用嘴堵住了她的嘴唇。 在枕边床头灯昏暗的灯光下,四季子把双臂合拢,遮在胸前。她的身体,在生完孩子后,便被空虚所压垮,和达郎一样逐渐腐朽……达郎拉开她交叉在胸前的双臂,把脸颊贴在她那平坦的胸口上。他感觉到一阵冰凉,身体几乎都被冷却了。 四季子趴在床单上。达郎用手指为她梳理着卷曲的头发,并吻着她的后背。她平时扎起来的头发现在放下来了,披散在后背和脸颊上。四季子先开口,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她的语气轻松柔和,就像在给钻进被窝的小孩讲故事一样。 “达郎,你终于也变成这里的人了。大家甚至连别人家的冰箱里放了些什么都一清二楚,却以为自己家里的事情不会被别人知道。不这么骗自己的话,就没法在这里生活下去。”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和你分开。” “喂,你以为我没发现吗?” “你说什么呀?” “你如果不是被捆绑在这片土地上的话,是不会对我这么留恋的。你对我的感情,并不是喜欢或讨厌,而是一种留恋。” 两人离开情人旅馆时,已经过了晚上十二点。达郎在距离家门口一百米的地方下了车,留下沉默不语的四季子一个人待在车上。达郎心想:“四季子一会儿回到家里,她家里人肯定不会以为她只是来送咸菜这么简单吧。她会以什么样的表情回到卧室,回到等待着她的丈夫身边呢?”四季子打开着车头灯,照亮了达郎走向家门口的小路。 家门口、走廊、房屋里的灯火全都已经熄灭了。达郎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上二楼房间。一推开门,却看见有人在黑暗中面向门口坐着。达郎吓了一跳,几乎要闪身躲开时,这才发现原来是玛丽,不由长舒了一口气。 “你,回,来,啦。” “快睡吧。我也要睡了。累。” 达郎脱得只剩一条内裤,随即钻进冰冷的被窝里。身体散发出四季子头发的芳香。他什么都不想,只想就这么沉浸在四季子的芳香之中。就快入睡时,玛丽钻到了达郎的身旁。达郎一碰到她那冰凉的手脚,立刻跳了起来。 “喂,你要干什么?” “Baby.” “孩子?” “Yes,baby.” “你饶了我吧。跟你能生出来吗?” “达郎,givemebaby。” 也许,父母提醒她说别忘了自己是用钱买来的媳妇?也许,他们还威胁她说如果不尽早生孩子就要被送回菲律宾去?也许,是她自己认为,只要当上母亲的话,从此在家里就有了一席之地?……这位决心在这片土地上勇敢活下去的少女,双手合在胸前,苦苦哀求。达郎却说道: “对不起,我做不到。今晚不行,以后也不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达郎并没有意识到,跟玛丽上床会让自己感觉到很悲哀。他也无暇考虑玛丽是否能理解自己说的话。他只是反复说着:“我做不到。” “Please,达郎。” 玛丽的声音带着哭腔。达郎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一个为了生存而被卖到异国他乡的少女。他只知道,自己和玛丽之间缺乏上床所必需的条件。 玛丽还是一个劲地反复说着“givemebaby”。达郎冲她怒吼道: “闭嘴!” 在这安静的房屋里,达郎的声音回荡在各个角落。 他推开紧紧地抱住自己的玛丽。同时,他在心中暗暗祈求四季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她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拒绝她那起了疑心的丈夫呢?能拒绝得了吗?……想到这里,他忽然意识到,想在睡梦中度过今天夜晚,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玛丽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达郎抱住她的头。至少,比起在楼下整夜没合眼偷听他俩说话的父母,他觉得自己还是能理解玛丽的。玛丽在达郎的胳膊里不停地抽泣着,直到入睡。 第二天一早,伸二在冷冰冰的牛棚里用扫帚清扫饲料盆。达郎走进来时,那些牛全都叫了起来——它们知道有吃的了。在牛叫声中,可以听到扫帚扫过水泥地的规则的声音。 达郎把饲料装到独轮车上,然后用铲子把饲料撒到清扫过的盆里。在狭窄的通道上,他和扛着扫帚的父亲擦肩而过。“爸。”达郎叫住了父亲。伸二回过头来——他脸上已经没有了当初把投资破产走投无路的儿子带回村里时的那种刚毅神情了。他身上开始散发出的,是平静地走向死亡的农村老汉的气息。 “什么事?” 见儿子怔怔地看着自己,伸二便问道。 “没,没事。” 达郎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刚才要叫住父亲。 祖父临死前,叮嘱家里人要把他埋在这片开垦的土地下。所以,他的骨灰应该被撒在了这房屋附近某处吧。达郎从来没有问过具体的位置。他也不知道,对于祖父把自己束缚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父亲是否顺从地接受、并且延续了下来? 在村落里,第二代人继承了第一代祖辈的遗志,固守家业,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好好地培养下一代。一方面,他们想让孩子自己选择喜欢的道路;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孩子能守护祖辈开拓的土地——这样的矛盾,反而造就了含混不清的家庭。在不彻底的放任主义下培养出来的下一代及其父母,最终失去了所有财产。这样的事实在是屡见不鲜。达郎之所以能回到村里来,应该感谢从来不轻信花言巧语的父亲。达郎心想:这种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安稳,也许不是人为的,而是来自于村落自身的生命力吧。 玛丽穿上肥大的旧长靴,走进牛棚里。达郎已经喂完饲料,钻到母牛的肚子下挤牛奶,准备留给牛犊子喝。他对着站在身后看自己挤牛奶的玛丽做了个喝水的手势,说:“杯子,杯子。”玛丽的表情忽然一下子亮了。她跑回家里拿了个大杯子过来。达郎把刚挤的浓稠的牛奶倒进杯里,递给玛丽。玛丽慢慢地喝着,脸红了。 两人给牛犊子喂牛奶。看见牛犊子撕咬奶瓶的奶嘴,玛丽就用刚学会的日语大声呵斥:“不,行!”不出一年,这些小公牛就可以作为食用牛拿去卖了。达郎来回看着正互相争抢奶瓶的玛丽和牛犊子,随即用双手抱住了玛丽的后背。 清晨凛冽的寒气逐渐消退。达郎走出牛棚时,正巧碰到了刚出门的四季子。她看见达郎,平静地微笑着。达郎心想:她第一次和自己上床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份悲哀吧。 “马上要准备过冬了。如果不嫌弃我穿过的话,我倒是找出了几件适合玛丽穿的旧衣服。你这人呀,就是不够细心。” “就你话多。” “我们彼此彼此吧。” 在达郎的注视下,四季子笑着坐上车。车开动前,四季子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在引擎轰鸣声中说道: “达郎,我喜欢你。” “我知道。” 达郎感到心里隐隐作痛。 当晚,玛丽清扫完浴室,钻进被窝里时,达郎紧紧地抱住了她。玛丽的身体一瞬间变得有些僵硬。随后,她也伸手搂住了达郎的腰。达郎解开她睡衣上的两颗纽扣,用手掌握住两个“小山丘”。 他祈祷着,要尽可能让玛丽幸福。来到这个家里,玛丽只能依靠他,他不愿看见她不幸。 玛丽的身体散发出一种类似于南方果实的香甜气味。她被动地躺着,任凭达郎的舌头来回探索。不久,她的腹部开始起伏,呼吸也逐渐变得急促。达郎用力,玛丽轻轻地叫了一声。 达郎产生了一种幻觉——搂抱着他后背的,是还穿着校服的四季子…… 牛棚二楼堆放青贮饲料的小屋里,玛丽坐在拆下来的门板边缘,眺望着远处的山脉。达郎曾经和四季子在这小屋一角温存过的地方,现在已经变得很宽敞。达郎看着身披羽绒外套的玛丽的后背。旁边,有白色的小虫子在飞舞——是雪虫。 “玛丽,你看,雪虫!” 达郎在玛丽身边坐下,摊开手掌,往空中抓了一把。他抓住几只白色的小飞虫,伸到玛丽眼前。 “雪,虫。” “嗯。很快就要下雪了。雪,snow,明白吗?” “Snow.” “这里会下好多雪哟。你等着看吧。” 一只雪虫落在了玛丽微笑着的脸颊上。达郎用指尖轻轻地把它弹走。 “那座山的对面,是我年轻时待过的地方。以后我带你去看看。” 他已经送走了一年又一年的雪虫。过去的日子,总会被掉落下来的薄翼所覆盖。苍白的时间,变得苦涩而美丽。那些再也飞不起来的羽翼,也落在了四季子的心里。 在雪虫的注视下,达郎和玛丽眺望着逐渐变暗的夕阳。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angnaiqing.com/knxwh/5653.html
- 上一篇文章: 会员福利送妈妈一束花,让她发个朋友圈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