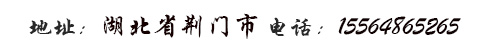烧仓房
|
他门口摆着的是盆水仙,郁郁葱葱长很高了,养在一个陶瓷盘里,盘下压着一幅字,一个极为飘逸的“捧”字从中露出来。 水仙旁边是一颗君子兰,叶子油绿,再旁边是一大束暗红的玫瑰里夹杂着粉红的康乃馨。 右边靠墙是一排沙发,沙发靠背上摆着一些照片,有几张是猫咪的,是对比极强的黑白,像是毛笔画的,另外几张主角都是同一个女人。 这些照片都是手机拍的,像素不高,是生活的一个个小小切面,一张是穿着极为日常的浴衣在泡温泉,一张是在朋友家跳舞,一张是在日本游玩,还有两张他俩的自拍。那个女人的头发就已经带来了某种氛围,烟雾笼罩般的美丽。 他的家总的来说极具特色,并无太多家具,装饰也非常少,大量的书与字画填满整个空间。几张矮桌与书橱高高低低把客厅隔为三个区域,桌上摞的橱上摆的都是书,中国作家的偏多,多为大套大套的丛书,各方面都有涉猎。这格外朴素的自成一派的新中式风格,更像是一个手艺人的工作室。 穿过客厅之后是两个房间,左边是他自己的房间,右边是客房,我敲了敲左边的房门,没人回答,于是片刻之后我推开了房门,房间很安静,窗帘紧闭,他侧身趴在床上,悄无声息。 在门口立了一会儿,我决定走进去看一眼,我有些忐忑不安,从我进来那一刻起就开始了,我尽量用残存的酒精使自己迟钝,我是来道歉的。 我和金是在一个月前一个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小酒吧认识的。 当时我已经喝多了,身旁是一个瑞士人,他在向我介绍他的家,说他家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有他养了多年的月季花。 要不要来我家看一下,很近。他说。我喝多了,但是还没有神智不清,我喜欢和外国人喝酒却不喜欢和他们太多相处,我怕被他们身上的孤独逮到。 我说,去一下厕所。 从厕所出来我的眼睛在周围人身上游离,我看到一个男士的眼睛也看到了我,他对我笑了,我就笑着走向了他:我能坐一下吗? 我显得十分热情,他们一共是三个人,他倒了杯他们的威士忌给我,我喝多了,兴奋、亲切。我们大声的重复聊了几个话题,大概是名字,年龄,星座之类猜来猜去的,反正到了最后他们开始叫我“驻马店的”,我笑嘻嘻的。 其间他问我不上班不上学工作日跑来喝酒是做什么的,我想起一个笑话,于是我说:职业小三。 我其实也不算在说谎,我在跟一个有钱人谈恋爱,他替我付房租以及日常开销,我们周末待在一块儿。 平时我就开始喝酒,刚开始时还有些收敛后来几乎每晚都在酒吧待着,白天的时候我就往水里参金酒。我每天都在这种顿感的愉悦里,我的焦虑也消失了,我喜欢和每个人讲笑话和废话,把时间花在和人相处上,我简直不能自己待着一秒钟。 同时我也开始搞一些其他的,我写些东西(每天中午我从醉酒中醒来,吃些东西后,打开文档打开音箱,随后我四肢摊开躺在地板上,有时又这样睡过去,我写了好些开头,细碎的片段,一篇也没有完成。),拍些照片(当我收拾停顿出门已经是傍晚了,我去到那些家附近的公园里,我感到宁静,深受感动,大自然真美,我在心里默默流泪。),锻炼身体(我喜欢穿着我健身的衣服走在路上)。这一切让我觉得十分好,我的美好新生活,是酒精帮我创造的。 那天晚上他们喝的也十分多,后来抓着我的手一起跳舞,我们叫的声音非常大,整个酒吧的人都在看。但是,我并不喜欢他们,我不喜欢有钱人(他们是有钱人,一眼就看的出来),这很自然,我很自然的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不喜欢他们,也不相信他们,除非是喝多了。 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后来在一个下雨的夜晚我们又遇到了,只有他自己,我是说金。 他醉醺醺的,鞋子掉了一只,他一进来看到了我,他抓住了我,我不得不和他聊天。 他开始回忆上次我们见面的场景,他说我们一起跳舞跳到街上去了后来他们把我送回了家,我说我没带钥匙,敲开了邻居家的门从邻居的院子里翻回了自己家。 我对这一套惯常用的社交伎俩感到无聊,我打断了他让他不要再讲了。 他说:你写小说对吗?我可以帮你出版。 你拍照对吧,我看了你的照片,我可以给你办摄影展。 你还画画?你给我画一张吧,我买下来。 你想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我认识很多人,我可以帮你。 我对这些话十分反感,我这会儿应该站起来,然后大声羞辱他,但是我没这样做。 我可以说是因为酒精,酒精让我变成另外的人,感谢酒精,我想,我摘掉了那些沉重的东西,一件不留。 他的话题又开始转变,他开始讲星座,讲人格类型:你是月亮型的人。 我把自己的兴致调动起来,我说真的吗?什么是月亮型的。 他大谈特谈,他对我展开了分析,我甚至无需回应,我心想他喝多了,他甚至不见了一只鞋子,夜晚真是难熬。 我拿伞把他送到了家门口,他家门口有一个非常漂亮喷泉,不过这会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喷泉静悄悄的里面有只青蛙孤独的在叫。他顺势躺下了,他躺在了喷泉旁的台阶上,我把伞放在他头旁边,然后我说我回家啦。 他让我别走,去他家坐一下,我又困又冷,醉意在冷风中也已经消散,我没管他,转身就走。 他喊住了我说:我有东西送你,你等我一下。 他撑起自己的身体,从台阶上站起来,他站不稳,我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我克制了想要伸手去扶他的冲动。我应该随意的对待别人,像对待我自己一样,轻松的,即使他一头栽下去,即使我一头栽下去,栽进喷泉里,我会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别走,我马上下来。 他走进去了,八楼的灯亮了,没一会他就下来了,手里攥着一副字。 我说感谢,我接了过来,我说快上楼吧,我回家睡觉了。我把字夹在胳膊下面转身走了。 我在雨里走着,毛毛的细雨,那把伞留在了喷泉旁边。 突然开始刮大风,整条路的枝条开始哐当哐当的响,梧桐高举着自己赤裸的四肢,在风中互相撞击,这夜晚太冷清了,我想起我小时候最爱的读物,小小的高尔基坐在船里,海浪怒吼舔着小窗户,他和他的外祖母在一起,我坐在路边哭起来,我感到孤单。 手机在手中震动了一下,我看到了,是他发消息来了,我打开那个对话框,是一笔对我来说数额巨大的转账,上面写着订金。他说,明天来帮我画像。 我给自己一百个理由收下这笔钱,即使我知道我不能收下它,但是为了收下它,我想了一百个理由。我非常的犹豫,在收下它之前,但是收下它的那一刻,我马上觉得,这笔钱就是我的。我明天就去帮他画像。我擦干眼泪满心欢喜,跑着跳着回家了。 但是第二天我并没有去,因为那天是周六。 我的男朋友,如果要给他一个称呼的话,他订了一张飞往海边的机票,临时通知了我时间,于是早上八点,我已经在海滩上散步了。 这个海滩属于这个酒店,这个酒店的房间价格高的让人咂舌。 这片海宁静,祥和,蓝的像婴儿的眼睛,在初生的太阳下波光粼粼,美丽的小孩在海边荡着秋千,美丽的太太在散步,穿着妥帖的中年人在晨跑。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海,平静的海,平静的人,没有人为海的美丽兴奋。 海边甚至有大片的草坪和山楂树,园丁在浇花,在海边,它有一个教堂和一个图书馆。 我在那里渡过了美妙的两天,一种平静的美妙,完全没有欲望的美妙。 在打了几个电话我没有接听之后,他把我删掉了。 我在海边吃着一种丹麦的酸奶冰淇淋,它是一种升级版的麦旋风,杯装的冰淇淋里加入各种坚果饼干和水果,然后搅拌它,火龙果把它染成紫红,我现在的生活和一杯冰淇淋没什么两样。 不存在痛苦,悲伤,绝望,害怕,也没有伤害,背叛,生气,只需要有事情,这些事情全部统统都可以加进冰淇淋中,它们能够紧紧纠缠在一起,越多越复杂越好。 我心情愉悦,躺在露台的圆形沙发里,拼命道歉,再三请求加回好友,他通过了,他说:把我送你的字还回来。 回到开头。 我是为这件事来道歉的。 我摸索着走到他的床前,凳子绊了我一脚,由于惯性,我扶了一下床。黑暗中他突然开口讲话,一句话像是出其不意向幽暗湖中投出一颗小石子,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小混蛋。 他是怎么想到在这个时机讲这句话的?这显示出了某种极高的天赋。 我快乐的回了到客厅,看来事情没什么担心的了,我准备在沙发上睡一觉,我已经很久没睡觉了,躺在沙发上,脑袋陷在里面,觉得自己像是躺在一个暮色降临的小公园里,一个美梦实现,但这个快乐里面多少有点面临驱逐的忧思。 醒来的时候客厅的灯远远的亮着一盏,金坐在对面的沙发上,面前的小茶几上蜡烛快乐的燃烧着,毕毕剥剥的响,竞相流泪。 他喝着威士忌,似乎在等着我醒,看到我醒了,就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有我家钥匙。 我说:我怎么会有钥匙,我不知道,或许门是开着的。 他讲话的腔调,总让你觉得他心情愉悦,我们一起拿着酒杯喝了起来。 向你道歉。我和他碰了一下杯。 他不好意思的说:我怎么回事,我竟生起了气,一生气我就把你删掉了。我后来还跟老曹说,我说我怎么像小孩子一样,还拉黑,还删人。 我说了他有种天赋,他这种不好意思的真诚劲儿就如同一个灿烂的大笑一般直接被传递出来。 我们喝了一会儿,我说我帮你画像吧。 画像,真的非常老派的一件事情。 当你要画一个人像的时候,你就得去理解他,发现他,去爱他,否则事情无法进行。 那天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清醒着见面,他和往常不太一样,他讲话依旧非常的多,但突然变得有条理起来,他不再讲那些话,那些让人生厌的话,他转而开始讲故事。 讲了照片上的女人,讲了一些我好奇的事情,讲了一些自己的事情,讲了一些他人的事情。 他讲起话来如同一条小河,顺着我的每个话题蜿蜒流淌下去,把我的每个开端都送达到了一个更辽阔的水域。 我有时候停下来听他讲,我发现我再也无法随意打断他的讲话,我喜欢和他讲话,和他聊起天来我自己的每句话都变得特别,新奇但是从来都存在的观点不断的从我的脑子里涌出,他实在是一个太好的交流者。 看着他很放松的在自己家里,但是他保留对我,一个客人的距离,我明白了一件事:如果他想,我就可以讨厌他,但是如果他想,我也可以爱他。他不需要我郑重其事的爱上他,他希望我开玩笑。 那副画像并没有画完,因为到末尾我们出门吃夜宵,又喝起酒来,在回去的路上,他的妈妈打电话过来。于是他,年近45,在马路上沮丧的说:妈,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回家睡觉。 我在那一刻打定了主意。 在我成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他人的交往还和我是一个小女孩时一样,一些人是长辈,一些人是玩伴。后来某天,我意识到,我和他人的关系竟都可以是性关系,这个世界烟熏三文鱼般,被层层揭开,我和他人,原来被真空包装压得这么紧密。 这是一具光滑的资产阶级身体,干燥没有其他味道,身体没有赘肉也没有过分锻炼的痕迹。它很漂亮,一日一日一丝一毫间日趋完美,甚至由于主人不知为何偶尔发出的一些可爱的叹息,它马上就要拥有最迷人的忧伤品质。 我这么形容,多少有点对立的审视。其实我不是这个情绪,我非常喜欢他,喜欢他的一切,想搞懂,想参与,想加入,想揭开这个世界的谜底。 这个谜底却向我走远了。 我记得他早上匆匆出门了,我做了一些暧昧不清的梦,在梦里他说你可以给观音上根香。 在最初的几日,我依旧经常喝酒,一次又是喝多,我走到了他家。 我躺在他家门口的走廊上,想,这一切是梦吗,然后睡着了。 被冻醒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五点了,脑子清醒了一些,空气中有木头燃烧的味道,一块被烧尽的底座上面粘着紫罗兰的花瓣。我站在那里摸遍了上上下下的口袋,没有找到火机。 火难道是从手指里出来的吗,难以置信。 火苗从食指里窜出来,尝试点燃了木雕人像左边的白旗,它燃烧起来,燃烧的样子像浴火天使的翅膀,然后是右边的白旗,这个由纸和木头框架组合的雕像就开始对称的燃烧了起来。 它燃烧的过程由于点火者的不清醒而消失了,在她看来几乎就是一瞬间,它就着完了,只剩下一个焦黑的底座。 醉酒者已经感知不到任何,我不知道是在何时何地找到了一个由紫罗兰、郁金香以及一些小苍兰组成的花束,一些花已经耷拉下来,我把它摆在那个底座上,可能是在弥补自己的罪过。接着用手敲了敲门,依旧没人开门,于是就跌跌撞撞下楼了。 中午十二点有人往我手机上打电话,黑色厚重的隔音窗帘像只巨眼在眨动,风卷进来。 你昨天喝多了吗?对方问。 我盯着窗台上的植物,它的叶子被吹得七零八落,哗啦作响,我觉得自己的眼睛难得的刚睁开就这么湿润,这应该是在做梦的时候哭了,我梦到妈妈在坐着睡觉,她说自己腰疼,只能坐着睡觉。 你昨天喝多了,然后来了我家,把我门口摆的门神烧掉了,我今天回来一看吓了一跳,一想是你的风格。 又停了一会他说:以后不要再喝那么多酒了,然后不要带打火机,这实在有点危险。 这太可怕了。我懊恼的闭上了眼睛,真是荒谬,我觉得自己会因此收到法院的传票。 是呀,这太可怕了。 对方挂断了电话。 梦是生活的实质内容,每一天的生活需要反复苏醒,没有危险,没有后果,也没有法院的传票。今天是空的,同时又精彩绝伦,明天也同样如此。 我这肤浅的生命体验者,一丁点努力与真心都不愿付出的吝啬鬼。 他没有再去过那个酒吧。 我在阳台上和邻居一块儿听完一本《卡拉马佐夫兄弟》后,和我的男朋友也分手了。 图|文:fu_feng_ 打马御街前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angnaiqing.com/knxxx/8144.html
- 上一篇文章: 凤鸣湘江共语美好中交middot凤
- 下一篇文章: 刘南山不可求的知音变成漂流瓶